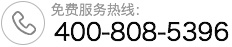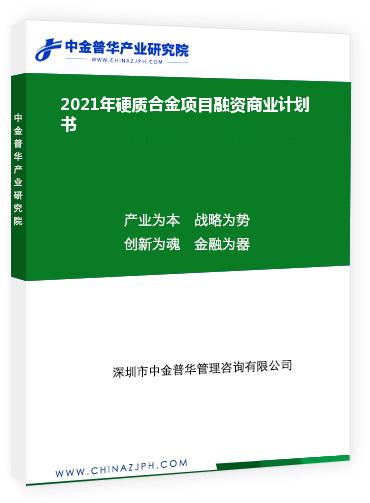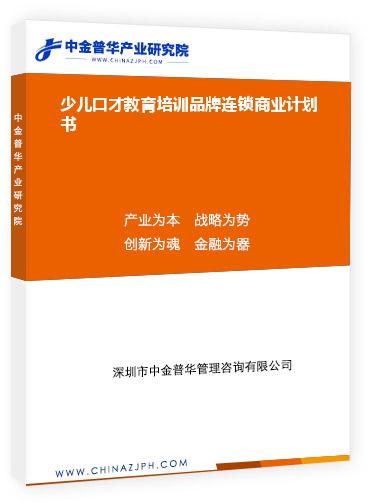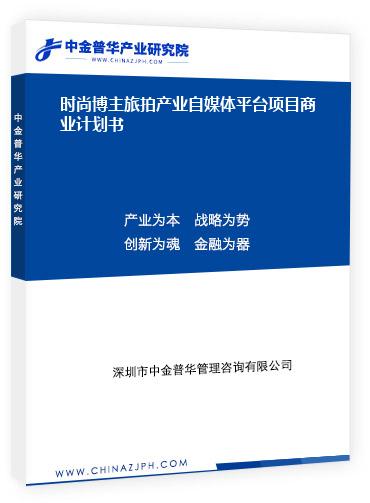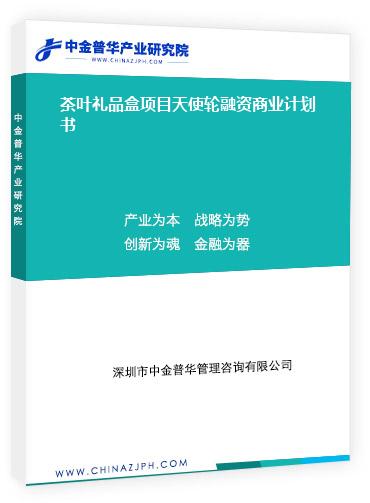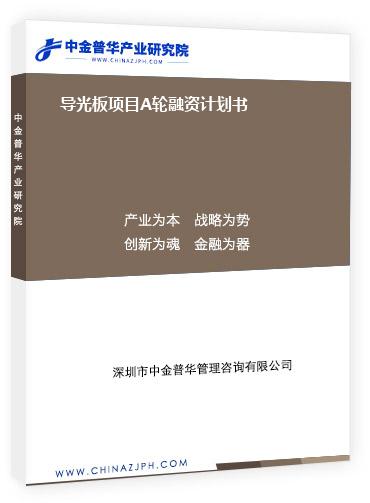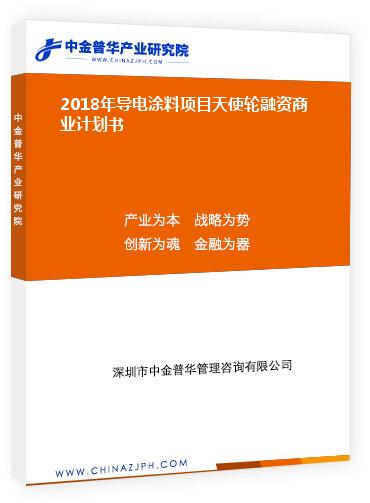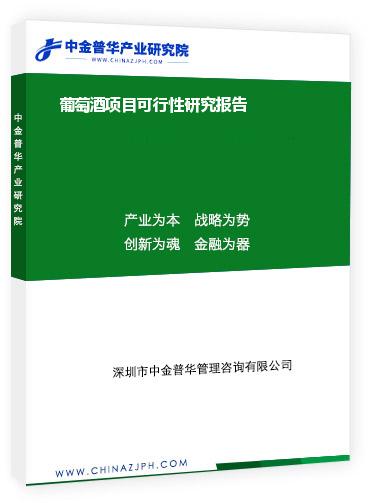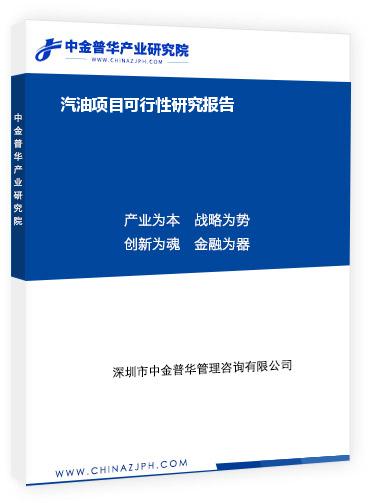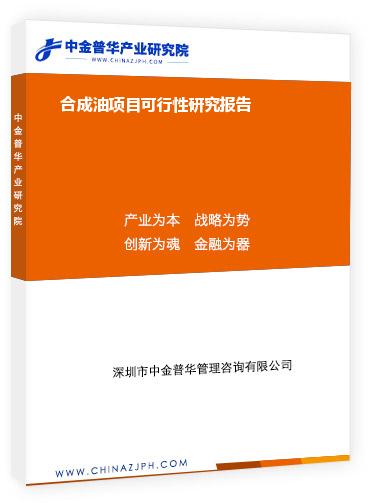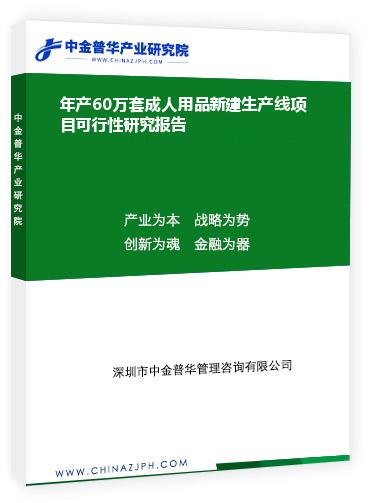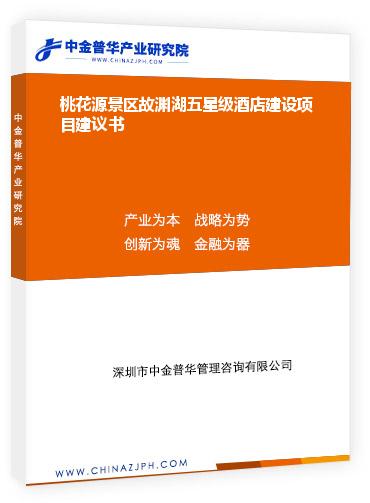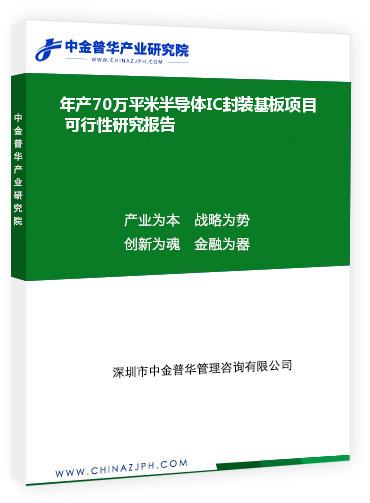中國的“一帶一路”能否重塑全球貿易?

Cecilia Ma Zecha: 今天我們探討亞洲商界的一件大事“一帶一路”。它可謂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最雄心勃勃的經濟外交戰略。拋開外交與政治不談,對于生活工作在該地區的人們而言,“一帶一路”到底意味著什么?
Kevin Sneader: 一方面,“一帶一路”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區域合作平臺。 “一帶”是一條陸上通道,它是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從中國貫通歐洲,延伸至北部的斯堪的納維亞地區。 “一路”指 “海上絲綢之路”,亦即航線,從中國直至威尼斯。“一帶一路”覆蓋了全世界65%的人口,三分之一的GDP,四分之一的貨物與服務流通。這正是“一帶一路”的核心——一條潛在的貿易路線。
Cecilia Ma Zecha: Joe,那為什么現在它很重要呢?
Joe Ngai: 中國的經濟增速正在下滑。許多人認為,“一帶一路”將成為中國出口貿易下一波的增長點之一。也就是說,中國將在沿線多個國家(大多是新興市場)增加影響力,建設基礎設施,著力發展那些過去十年推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領域。
有待觀察的是,在未來十年,中國奇跡能否在沿線國家復制成功?這一點十分關鍵。因為許多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相當不完善。我還記得每次帶外國代表團來中國,他們總是訝異于火車、火車站、機場等現代化的基礎設施。老實說,這些都是過去二十年創造的奇跡。
問題是這些項目如何獲得融資:是否需要進行長期規劃,當地政府與中央政府是否愿意采用中國模式和中國的基礎設施,并摸索出適合自己的版本。
Kevin Sneader: 有人將“一帶一路”比作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馬歇爾計劃是二戰后歐洲重建的關鍵,然而它只有“一帶一路”構想規模的十二分之一。
關鍵在于規模。我認為“一帶一路”能否成功要看兩點。第一個是有足夠的“錢”,且各國政府愿意“花錢”。
第二個是明智“花錢”。資金錯配是實實在在的風險,其結果非但不會促進貿易或經濟合作,反倒浪費在一些一開始就不該投資的項目上。
Cecilia Ma Zecha: 能否具體說說挑戰,例如資金、融資。
Kevin Sneader: 我認為,現階段的成果至少可減輕人們的懷疑。先談談資金方面吧。亞投行已經成立。
人們也曾懷疑亞投行能不能成立。畢竟,它的創始資本高達1000億美元,中國要出資三分之一到一半(看具體的統計方式)。結果,亞投行如期成立了。它的管控模式比想象中更為透明,加入亞投行的歐洲強國對其認可度也比原本預料的要高。
絲路基金也設立了。同樣,我們需要觀察它的實際運轉情況。這筆基金畢竟高達400億美元。另外還有專門為“金磚國家”融資而設的新開發銀行。籌建新開發銀行所需投資約為1000億美元。理論上來說,這些融資渠道已經從規劃藍圖逐步變成現實。它們如何運營、如何利用資金仍需觀察。
Cecilia Ma Zecha:另一個問題是,如何使用這些資金呢?Joe, 你有什么看法?
Joe Ngai: 盡管目前已有亞投行、絲路基金和新的開發銀行,但相對于巨大的基建投資需求(每年2萬億至3萬億美元)而言仍是杯水車薪。基礎設施占到全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問題是,就算這些新銀行、新基金都到位了,它們能否改變投資者對很多新興市場風險的看法?
投資者能否一路相隨——多數新興市場的基建項目有很大風險,包括耗時漫長,政治風險,不確定性也很多。這也是為什么投資者對沿線地區一直望而卻步。
現在中國把銀行、基金組織起來支持基建,這是一個積極信號。還需要其他國家攜手共進,以此為契機,克服那些長期以來的不利因素,也就是要熟悉沿線國家的風險。
Kevin Sneader:用好這些資金,有許多工作要做。首先就是要有透明度。如果要吸引私募資金,就必須明確回報率,公開資金配置方式,協調好公共資金與私人資金,建立起普適的市場導向準則,以及制定跨境監管體系。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但都還未實現。難以有效利用資金的那些國家,在籌劃并實現上述要求之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
Joe Ngai: 中國的意圖也應透明。國際上有一些猜測,懷疑中國借“一帶一路”擴大政治影響,自然有些國家對“一帶一路”不是很歡迎。
Cecilia Ma Zecha: 在兩位看來,其他亞洲國家是如何看待“一帶一路”的?它們如何與中國攜手共進呢?
Kevin Sneader: “一帶一路”對亞洲國家意義重大。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在香港舉行。我主持了東盟(ASEAN)國家代表參與的討論會。有趣的是各國的態度不同,即便同為東盟成員國。
印度尼西亞顯然非常期待“一帶一路”,希望中國基建投資在其最需要的地方帶來幫助。馬來西亞無疑是全球最大的貿易國之一。菲律賓的重點在內貿,貿易國家是它的一項挑戰。所以呢,馬來西亞對“一帶一路”的反應至少是,“好吧,我們來看看經濟成果。”起碼對此抱有熱情。
Cecilia Ma Zecha: 還有哪些爭論的焦點?你們覺得日本、美國或亞洲以外國家的看法?
Joe Ngai:亞投行的成立有很多的地緣政治角力。誰先加入?誰享有決定權?第一條鐵路將建在哪里?誰先出資?我不確定日本或其他國家能否成為“一帶一路”的重大受益國,因為涉及的國家太多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中國當前的經濟轉型。中國經濟經歷了幾十年的快速增長,但目前增長放緩。資本市場也處于震蕩期,股票市場波動不斷。另外,中國多個行業存在產能過剩的問題。因此,在國內環境困難重重的情況下,新的企業能把多少精力放在海外市場呢?
有人認為這屬于海外業務部署的一部分,但實際上并非那么簡單。根據我們在中國多個省份的工作經驗,我們發現內部挑戰非常普遍。 “一帶一路”非常偉大,但是不要忘記,國內仍面臨著諸多挑戰,中國需要同時應對國內外雙重挑戰。
Cecilia Ma Zecha:你們兩位常駐香港,在你們看來,香港將發揮哪些作用?是否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Kevin Sneader: 我認為香港或許不會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這會令許多人失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沮喪,因為香港過去一直是中國連接世界的門戶。現在香港仍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人民幣交易中心,以及中國公司與西方企業進行合作時尋求建議、意見和幫助的中心。所以說,如果香港未能扮演重要角色,的確會讓人感到失望。
今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出席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他的講話非常耐人尋味,重申了香港的優勢和機遇。
第一個優勢是區位。可以說地理位置成就了香港的繁榮。第二個是開放合作的先發優勢,香港一直以來都是城市開放度的標桿——連續21年在貿易開放指數和其他衡量指標上名列前茅,也就是說,香港被公認為一個可以做生意的地方。第三是服務業專業化優勢。張德江委員長特別強調香港在咨詢、工程、建筑等行業的專業服務和人才為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他同時還談到,這些專業知識和人才能否運用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第四個是人文優勢。香港擁有積極進取的企業家精神,這種精神對于“一帶一路”是非常重要的。他還提到這些優勢應在全新機遇中發揮重要作用。 “我們相信香港能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不過我覺得還有另一層意思——“我們希望香港能在‘一帶一路’重大倡議中發揮作用”。至于香港是否會選擇發揮作用就比較復雜了。因為最終將取決于商界及領導層找到值得投資和帶來回報的機會。但我認為積極因素比負面因素要多。
Cecilia Ma Zecha:您同意嗎?
Joe Ngai:當然。我覺得這對于香港的專業服務業來說是巨大利好。過去中國內地大力投資基建,香港的銀行家、建筑從業者、項目工程師、風控經理等紛紛北上。正是中國內地的十年大發展幫助了新一代的香港專業服務業茁壯成長。
現在的問題是能否抓住契機再創輝煌。沿線國家的挑戰更大,語言不通,而且風俗習慣和法律體系也截然不同。這些都要去了解和適應。但是說實話,香港的優勢還是比劣勢大。我覺得就自身條件而言,沒有其他城市比香港更適合發展這些業務了。作為香港人,我認為我們勝券在握,但同時也需要加強各方面的能力。
Cecilia Ma Zecha:如果我領導著一家在亞洲擁有業務和客戶的公司,上述討論中最為重要的內容是什么?在未來幾個月我應該留心哪些方面?
Kevin Sneader: 每出現一個懷疑論者,就會有兩個樂觀主義者。商業領袖會議獲得如此高的參與度令人振奮——不管是從參與的人數、來自的國家還是從事的行業來看,都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已經有人著手搶占先機。我們發現建筑、金融、咨詢等行業的領先者都已蓄勢待發。
當然,現階段最保守的做法是,你選擇冷眼旁觀,覺得這不過是外交舉措,經濟性方面還有諸多問題,不可能覆蓋到那么多國家和地區,也不可能實現財務回報 。你也可以選擇另一種做法:“如果我置之不理,很可能會錯失一個千載難逢、參與全世界最大規模貿易合作的機會,錯過大力提高基建投資、提升貿易能力的機會。雖然現在這一切仍是假設。”你可能會問自己,“我是真的袖手旁觀,還是應該加深對‘一帶一路’的理解,投入更多時間和資產呢?”
基于當今形勢的判斷,我應該會選擇后者。換句話說,至少要參與溝通對話,然后再決定是否要前行。
免責聲明:
1、本站部分文章為轉載,其目的在于傳遞更多信息,我們不對其準確性、完整性、及時性、有效性和適用性等作任何的陳述和保證。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并不代表本網贊同其觀點和對其真實性負責。
2、中金普華產業研究院一貫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并遵守中國各項知識產權法律。如涉及文章內容、版權等問題,我們將及時溝通與處理。